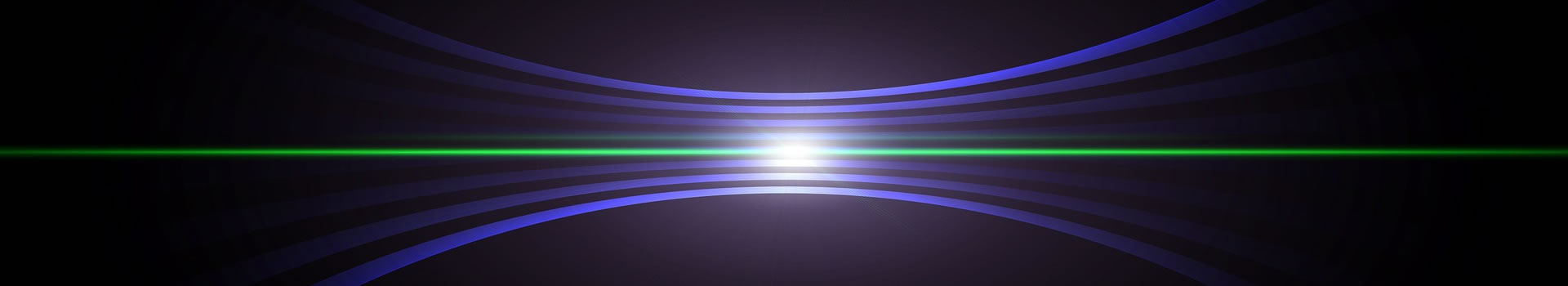
夜班刚过三小时,我正低头算着账,突然听见门口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。
一深一浅的节奏,还是那个女孩,每次都走在后头,像每一步都犹豫了半天才迈出去。
我抬头看向玻璃门外,那两人又来了。
王有财,头发还是染得金黄,走得快,手里攥着一摞现金。
后头的蒋子欣低着头,一副不太想被人认出来的样子。
她今天穿了件浅粉的卫衣,袖子长得快盖住手了。
“老地方,208。”王有财把钱往台上一扔,语气不太耐烦。
我伸手接过钱,无意间扫到她手腕上几道细长的伤口。
她一见我看见了,赶紧把袖子往下拉,动作急得有点慌。
这是他们第三次来了。
每次都选周五晚上登记,等周日中午才退房。
可今天,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
我叫李嘉园,在这家职高旁的小旅馆做前台已经两年了。
说不上啥好工作,但起码稳定,店老板郭淑芬人不错,工资从不拖,也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

唯一让我有点别扭的,是这里的客人。
多数是职校学生、工地上的工人,还有些人,我看了就不想多打听。
王有财和蒋子欣,是一个月前第一次出现的。
那天中午我刚值完班,正趴在床上打盹,门突然被敲得砰砰响。
我迷糊地开门,站门口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,头发金得扎眼,穿着个篮球背心,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。
“有房没?要最安静那种。”
他说话时还不停往屋里看,整个人有点焦躁。
“有,二楼最里面的208,一晚八十。”我照例回答。
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。
瘦瘦小小,扎着马尾,穿着一件快滑落的校服外套。
眼睛挺大,却有点没神,像是藏着什么怕人的事。
她一路低着头,脚步轻得几乎没声。
“身份证拿来。”我伸手要。
王有财先甩了自己的出来,又用胳膊肘碰了碰女孩:“子欣,快点。”
她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出学生证,怯生生地递过来。
我扫了一眼——市职院,幼教专业。
确实还在读,挺小个姑娘。
登记完,他们俩就上楼去了。
我又回台前坐着,可心里却堵得慌。
干这行久了,什么人都见过。
一个眼神、一句话,有事没事的都能分出来。
这俩人看着就不对劲,哪里都透着别扭。
那天我排夜班,快十一点的时候,楼上传来点动静。
不是很吵,但那种压着嗓子吵架的声音,在夜里听着特别刺耳。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拿起钥匙上楼去了。
店里有规矩,不能打扰其他客人。
走到208门口,那边突然就没动静了。
我敲了敲门。
“没事,电视声音开大了。”王有财在门里回,声音挺急。
我靠门站了几秒,里面确实安静了。
正准备走,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特别轻的哭声,像是有小动物受伤了一样,闷闷的、断断续续的。
第二天一早,我特意提前了半小时上岗。
才七点五十多,王有财就从楼上走下来了。
头发乱糟糟的,眼圈发青,像是一宿没合眼。
“一共多少?”他边问边从裤兜里掏出一叠揉皱的钞票。
“两晚,一百六。”我一边记账一边瞥了他一眼。
他埋头数着钱,我随口问了句:“你女朋友呢?”
“她先走了,要上课。”
他说得飞快,连眼神都没抬一下。
可我分明记得,昨晚零点之后整层楼都安安静静的,压根没人下过楼。
更何况今天是周日,职高哪来的课?
他拿了收据就往门口走,临走前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那眼神,说不清是防备还是犹豫。
下午我下班,去职高旁边的小卖部买点洗漱用品,没想到在超市外碰见了蒋子欣。
她一个人坐在水泥台阶上,手里拿着个面包,却只是握着,没吃一口,眼神空空地盯着街口。
阳光透过行道树落在她身上,一闪一闪的。
我凑过去,小声喊了句:“子欣?”
她像被吓着似的猛地抬头,看到是我后,立刻慌了神,站起来就想走。
“等等。”我喊住她,“你脸怎么回事?”
她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下脸颊,语气含糊,“没事,走路没注意摔的。”
说话声音闷闷的,像刚哭过,眼角还残着点红。
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小卡片递给她,“有事可以找我,我就值旅店前台。”
她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接了过去,低声说了句:“谢谢姐姐。”
然后她头也不回地钻进人群,很快就没影了。
我站在那,看着她瘦瘦的背影,心里闷得厉害。
她也就十七八的年纪,按理说这个年纪该坐在教室里写作业,要么和同学看个电影吃点小吃,而不是窝在小旅馆,满脸心事和伤。
过了一周的周五晚上,他们又来了。
刚走进店门,我就觉出了不对。
蒋子欣剪了头发。
原本垂到腰的长发,现在成了刚过肩的短发。
整个人气质也变了,眼神空空的,像是彻底放弃了什么。
“还是208?”我问王有财。
他点点头,随后转头对她说:“你先上去,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她拿了房卡,什么都没说,就转身上了楼。
我注意到她走路一瘸一拐的,像是脚崴了,或者更严重。
等她走远了,王有财忽然凑过来,压低声音说:“这几天要是有人来找蒋子欣,就说不认识,也没见过。”
我心头一紧,问他:“谁会来找?”
“谁都别提,谁都别认。”他一字一顿,盯着我看,“听懂了吗?”
说完,他从口袋里抽出两张百元钞票扔到柜台上。
“给你点辛苦费。”
我盯着那两张票,指尖发紧。
干这行的,给点小费的不少,但像这样直接砸钱封口的,我头一回遇上。
我把钱推了回去:“不用。”
他脸色沉了下来,眼里多了一丝狠劲,“我劝你收下,别多管闲事。”
说话虽然轻,但句句都透着威胁。
他甩下这句话就往楼上走,脚步一声比一声重,像踩在我心口上。
我站在前台,心里乱成一团,子欣那张麻木的小脸,还有她一瘸一拐上楼的背影,一直在脑子里转。
那晚我翻来覆去,怎么都睡不着。
凌晨三点,走廊里突然传来几声闷响。
像有什么重东西砸到墙上,一声、两声、三声……紧接着是那种压着嗓子的哭声,尖而细,听得人心里发毛。
我心头一紧,披上外套冲上了楼。
走到208门口,我屏住呼吸,耳朵贴近门板。
“再哭就别怪我了。”王有财的声音低沉,带着狠劲。
“我想回家……我想找妈妈……”蒋子欣的声音哆嗦着,几乎听不清。
“家?你早就没家了。”王有财冷笑,“不想吃苦就给我乖一点。”
我站在门口,指甲死死扣进手心,呼吸都粗了。
这根本不是谈恋爱,是明晃晃的威胁和操控。
我一边掏出手机准备报警,一边后退了半步,正准备按下报警键,楼梯那边传来动静。
是郭淑芬,店老板娘。
她穿着睡衣,一边踩着拖鞋上楼,一边皱着眉往这边走。
“小嘉,这么晚你还在楼道干嘛?”郭淑芬的声音从楼梯那边传过来,语气里带着点疑惑。
她四十多岁的人,平时打扮一丝不苟,就算半夜出来,睡衣都熨得平整,头发用卡子夹得利利索索,连口红都没掉色。
她慢慢走过来,脚步稳得很,看起来啥事都难不倒她。
“楼上有点动静,我上来看看。”我收起手机,语气尽量平静。
她走到208门口,侧着耳朵听了听,屋里一点动静也没了。
“估计是电视开太响了。”她语气淡淡的,“小年轻,有时候爱闹腾。你回去歇着吧,别太操心。”
她说得客气,但那“少管闲事”的意思,藏都没藏。
我犹豫了下,还是开口问了句:“老板娘……那姑娘,看起来不像满十八了,她真成年了吗?”
她顿了一下,随即恢复过来,面不改色地说:“她学生证登记过,写的是2006年,按这年龄算,刚好成年。”
她语气很稳,紧接着语重心长地说:“小嘉,你干这一行也不是第一天了,最基本的规矩是什么?”
我低声应了一句:“什么?”
“少问,多做。”
她看着我,眼神不紧不慢,“有时候该闭嘴就闭嘴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是为了好过。”
说完,她拍了拍我肩膀,表情还是和气的,可整个人像罩着一股说不出的压迫感。
我点了点头,嘴上没反驳,心里却七上八下的。
回到一楼后,我翻出登记本,找到她上次留的那份学生证复印件。
上面写着2006年出生,职业技术学院幼教系,资料看着没啥问题。
可她那身板,那一看就还没长开的模样,说她成年了我是真信不下。
第二天早上退房时,我特意留了点心。
蒋子欣是一个人下来的,走得特别慢,左手还扶着腰,看起来像是那地方被撞了。
她嘴角也破了点,伤口还带着血,看着挺新鲜的。
“子欣。”我轻声叫了她一下。
她抬起头看着我,眼神里闪过一丝希望,就像有人突然朝她扔了一根救命绳。
但那光很快又熄了,眼神瞬间又暗了下去。
“姐姐。”她声音轻得跟纸似的。
我从抽屉里翻出一瓶碘伏和几张创可贴递过去,“拿着,别让伤口感染。”
她接过去时手都在抖,眼圈也红了。
嘴唇动了动,像是想说什么,最后却什么也没说,只留下一个复杂的眼神。
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感激、难堪、恐惧,还有一丝快被压垮的求救,全混在一起。
下午我把前台的活交给同事,自己窝在员工宿舍发了半天呆。
最后,我下了个决心——我要搞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情况,她跟王有财之间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我先去了职业技术学院。
说是去找朋友,其实是混进教学楼打探消息。
跟几个学生闲聊后,我确认了她确实是幼教专业的,但据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上课了。
“她家里出了点事,休学了。”班主任语气挺随意的。
我问她到底出什么事,她摇头说:“休学申请上就写了‘家庭原因’,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离开学校后,我又去了派出所。
我用旅店员工的身份当借口,试探性地问有没有年轻女孩的失踪报案。
“有几个,但都是成年人,大多是跟家里闹矛盾自己跑出来的。”
值班民警边翻记录边说,“你问这干啥?”
我随口编了理由,说最近店里来了个女孩感觉不对劲,怕将来惹麻烦。
他也没细追,只说没线索不好定性,也不好处理。
但我的心更乱了。
如果她真是被逼的,家人怎么没人找?学校就草草批个休学了事?
当晚我回到旅店,发现郭淑芬还没走。
她平时晚上很少出现,大多数时候店里都是我们几个轮班。
但那晚她不光在,脸色还不太对。
“小嘉,过来一下。”她站在办公室门口喊我。
屋里光线昏暗,空气里混着烟味,有点呛。
她坐在椅子上,一手夹着烟,神情紧绷得让我一进门就有点慌。
“听说你今天去学校打听事了?”她开门见山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,但表情还算稳:“就随口问问,没别的意思。”
她没接话,只是吸了口烟,吐出的白雾在灯光下飘着。
“小嘉,你跟我两年了,我一直把你当自己人。但有些事,你真不该碰。”
“我不是多事,就是觉得那个女孩……”我刚张嘴,她就打断了我。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,你觉得那孩子不对劲,对吧?”
我没答话,算是默认了。
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语气低了下去,“这年头事儿太多,哪有那么清楚的对错。”
“那您到底什么意思?”我听着她话里有话,有些不明白。
她回头看我,眼神沉得厉害。
“她不是被逼的,是她自己愿意的。”她一字一句地说。
“她……自愿的?”我几乎不敢信自己听到的话。
我盯着她那张淡定的脸,脑子里一片乱麻。
“自己愿意?”我下意识重复了一句,声音比我想象中还冷。
郭淑芬没理我,把烟头按进烟灰缸,动作慢悠悠的,却带着一股压人的劲儿。
“有些人,你给她一条路,她不走;
你给她一条沟,她自己跳下去。
我们看着难受,但她可能觉得这是命。”
我听得心里发麻,脑子里全是蒋子欣那张脸——低着头,眼神躲着光,嘴角带着血,走路还一瘸一拐。
那叫“愿意”?要真是心甘情愿的,眼神不会那么空,声音不会那么细,手不会抖成那样。
“老板娘,她才多大啊?”我忍不住问。
郭淑芬瞥我一眼,“十八了,该对自己负责了。
你以为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,安稳干个前台,两年没出事?”
她话说得轻,却像一记一记敲在我心上。
我嘴巴动了动,没吭声。
“她来找我,不是第一次。”
郭淑芬的语气忽然低了点,“去年冬天,冻得手都裂了,穿一件不合身的旧棉袄,说她想找份住店的活儿。
我那时候看她可怜,介绍去隔壁旅社干清洁。”
我一愣,“你那时候就认识她?”
她点了点头,笑得意味深长,“干了不到一个月,自己跑了,说那边太累,工资还低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就没消息了。直到一个月前,她带着王有财过来登记,我才反应过来是她。”
郭淑芬吐了口烟,“你说她要是真想脱身,会一声不吭又跟着回来?”
我一时说不出话。
办公室里陷入沉默,只有窗外偶尔几声车子掠过。
“她知道怎么上网、怎么报案,也知道旅店每个监控角落在哪儿。”
郭淑芬敲了敲桌子,“可她一次都没试过。”
我站在门口,指尖紧紧绞着衣角。
“你要是真想帮她,”她声音低了些,“那就别再查下去了。
她要开口了,我们才好插手;
她不开口,咱就算报警,也只是‘俩成年人之间的私人感情纠纷’。”
“可她……”我咬着牙。
“她没让你救。”郭淑芬盯着我,一字一顿,“你记住,这是重点。”
我没接话,站在那儿,感觉身上像压着块石头。
郭淑芬把烟灰缸往旁边推了推,掸了掸睡衣的袖口,语气听上去像聊家常一样:“你别看她现在那副样子,以前还挺有主意的。
上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,据说初中那会儿想考重点高中,最后没去成。”
我看着她,“为什么?”
“家里欠债,父母为了减轻负担,干脆让她报职高。”
郭淑芬眼神扫了我一眼,“她也没闹,照样去上学、实习、参加活动,外人看着特别懂事。”
我心里一震,之前看她的学生证是幼教系的,我还以为她是那种从小喜欢小孩的姑娘。
郭淑芬轻笑了一下,继续道:“后来她妈妈生病住院,父亲跑债跑路,她一个人扛着。
听说靠兼职做过便利店、奶茶店、超市收银……能干的都干过。”
我喉咙像被什么哽着,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“再后来,人就开始不太见人了。”
她顿了一下,“去年有段时间,她在网上卖照片、接视频,圈子里流传过她的号。”
我下意识抬头,惊了一下:“你说……她做过那些?”
郭淑芬没有直接点头,只是慢慢站起来,靠着窗框,“我们是旅店,什么人都见过。
小姑娘把自己卷进去,一开始可能是为了还债,也可能是为了活命,但等适应了那种生存方式,有时候你给她正常的路,她都不走了。”
“可她不是没选择……”我低声说。
“选择?你能保证她现在出去还能找到工作?
她这模样,一进面试人家就把她当问题学生。”
郭淑芬看了我一眼,“社会没那么多同情心,也没人专门扶一个烂泥巴上墙。”
我听着这话,胸口闷得像被石头压着。
“那你就眼睁睁看她被人当成工具使唤?”
“你觉得我想吗?”郭淑芬罕见地叹了口气,“我就这么点地方、这么点资源,能护她一天、两天,那她之后呢?
你以为她真的想回家?她家那点破事,你不知道。”
我没问。也许是不敢问。
“我不是圣人,也救不了所有人。”
郭淑芬把窗帘拉上,转身看我,“可我起码知道,什么时候该闭嘴,什么时候该动手。”
我咬着牙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“你也一样。”她拍了拍我肩膀,声音低了点,“别让一时热血毁了你自己。蒋子欣的命,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到这儿的,不是你带她来的。”
“可我要是现在什么都不做,那是不是就和你一样,只看不管?”
郭淑芬没有马上回话,烟灰缸里还飘着未散的烟丝味。
“你觉得你能管,她真愿意让你管?”
她回了这么一句,语气很平,但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里。
我低着头,从她办公室出来,脑子还是懵的。
那天晚上我值夜班,整整一夜没合眼。
有几个工地工人半夜来订房,说话大声,我强撑着笑脸招呼他们,手却在柜台下不停打颤。
凌晨快五点时,我实在熬不住,拿了毛毯躺在员工休息室的椅子上。
闭着眼,却怎么都睡不着。
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蒋子欣的样子——她坐在台阶上捏着面包发呆,嘴角带着血、眼里藏着求救;
还有她退房那天扶着腰下楼,一声不吭地收下我递过去的药水。
我怎么也想不明白,这么小的一个姑娘,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
她到底是“自愿的”,还是“没得选”?
我不知道。但我越想,心里就越难受。
那天之后,我再也没见过蒋子欣。
不出意外地,她和王有财没再来旅店。
郭淑芬什么都没说,该上班的上班,该结账的结账,日子照旧。
我每天机械地值班、换床单、记账单,眼神总是不自觉地往208那方向飘,但门牌一直冷冰冰地挂着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直到大概过了半个月,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,派出所来人了。
两个民警站在前台,说要调旅店的监控,说涉及一起未成年女性被胁迫的案子,怀疑有人利用假证件登记入住。
我心头猛地一紧。
我看向郭淑芬,她的表情没什么波动,只是让他们等了一会儿,然后亲自去打开了监控主机。
整整一下午,她陪着民警把近两个月的录像翻了一遍。
我站在一旁,心跳一直没下来。
208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。
蒋子欣的脸被拍得不甚清楚,但那瘦小的身影、一瘸一拐的脚步,还有她几次低头捂着肚子的动作,一看就不正常。
那两个警察互相看了看,没有多问,只是拿了部分拷贝走了。
他们离开前其中一个民警问:“你们有人认识这个女孩吗?
她叫蒋子欣,之前疑似有失踪记录,她妈妈最近重新报了案,说联系不上她三个月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郭淑芬却很平静,“登记过,但只看身份证复印件,没注意其他。”
民警点了点头,留了联系方式:“这事儿可能要走个程序,麻烦你们配合下。”
晚上我去翻登记本。
蒋子欣那一页还在,压在厚厚几本记录中间,信息写得规规矩矩,名字、生日、学校……每一栏都填得完整。
我盯着那张复印件发了好一会儿,最终还是拿出来,用透明胶粘在了柜台下方的抽屉里,锁起来。
接下来几天,旅店没什么变化,生意照做,该来的还是会来。
郭淑芬也没再提那事,只是偶尔看我一眼,像在确认我有没有什么反应。
第五天傍晚,旅店来了一个陌生男人,穿得整整齐齐,提着个袋子,说是找人。
“我妹叫蒋子欣,以前在这儿住过……她以前可能不太愿意回家,但她妈最近身体出了事,我想碰碰运气。”
我看着他,犹豫了几秒,还是让他进了休息区坐下,倒了杯热水。
他说蒋子欣初中其实成绩很好,是家里变故把她推向了边缘。
父亲跑路后,她妈靠给人缝缝补补养着她,一直咬牙供她读书。
后来她说要自己生活,就没人再管得住了。
“她从来没告诉我们她过得怎么样。”
那男人声音低哑,“我也不知道她最后是靠什么过的……直到上个月,我妈在旧手机里翻到她发来但没发出去的短信,才知道她一直躲着我们。”
“短信里说什么?”我问。
他抬起头,眼眶发红:“她说,对不起,等我好一点,再回家。”
我低下头,鼻子有点发酸。
他走之前,把手里那个袋子递给我。
“里面是她以前喜欢的东西……粉色卫衣、旧照片,还有我妈做的红糖发糕。她不回来也没事,只要她知道家里还开着门。”
他转身那刻,我忽然想起那天下午,她坐在台阶上握着面包发呆的模样。
那个目光,像一只站在风口的小鸟,风一大,就会飞走。
一个星期后,警方打来电话,说已经找到蒋子欣。
她是在另一个小城市一家棋牌室里被发现的,脸色差、精神恍惚,还带着点旧伤,但人还算安全。
她一开始不肯说话,直到警方联系上她母亲,她才点头承认了身份。
没细说她这几个月经历了什么,只是警方那边说,会安排她接受心理评估和相关保护程序。
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,心头压着的那块石头终于稍稍松动了一点。
郭淑芬知道后,只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
第二天,她在后厨煮了一锅汤,还破天荒让人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。
我端着那碗汤,看着冒着热气的瓷碗,忽然想到一句话。
不是所有掉进泥里的姑娘都能爬出来,但只要她还记得往上看的方向,总会有人,在不远的地方,把手伸出来。
哪怕她不伸手,哪怕她还在犹豫,也没人会真的放弃她。
也许,这就是我们这些“前台”的意义——我们不拦她走的路,但至少,在她想回来时,还能留盏灯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