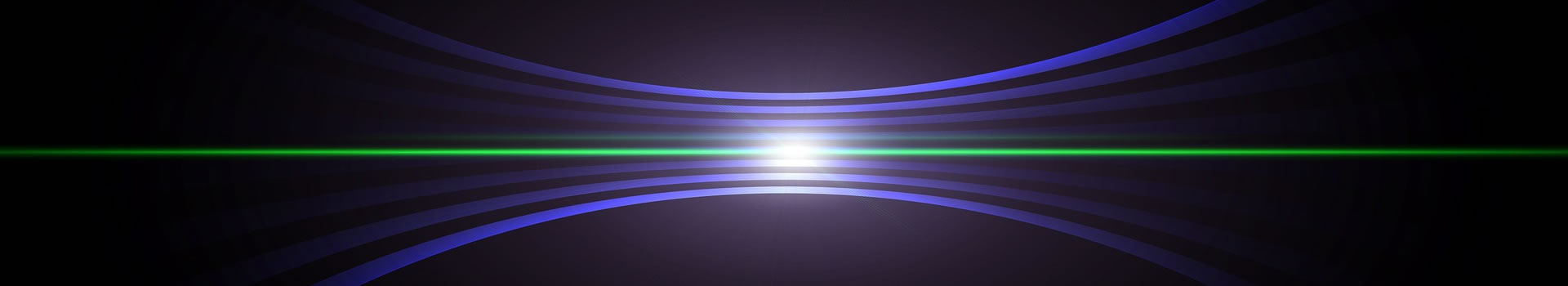
我跟你说,在踏上叙利亚的土地之前,我觉着自己也算是个见过点世面的中国背包客。什么印度恒河边的“人生终极套餐”,什么埃及金字塔下缠着你兜售草纸的小贩,我都当笑话讲。
但叙利亚,好家伙,它第一天就给我上了一课,直接把我这点“见识”碾得粉碎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大马士革的午后,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。我热得舌头都快吐出来了,冲进一家街边小卖部,指着冰柜里唯一认识的牌子——可口可乐,用蹩脚的阿拉伯语加全身比划,买了一瓶。
拧开盖子,“呲”的一声,那气泡升腾的声音,简直是天籁。我一口气灌下去半瓶,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正当我心满意足地准备付钱时,老板伸出了几个手指。

我掏出刚换的一大把叙利亚镑,数了半天递过去。老板笑着摇摇头,又比划了一下。我当时就懵了,难道不够?我这可是按黑市汇率换的钱啊!
旁边的当地向导看不下去了,凑过来低声说:“哥们,这一瓶可乐,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两天的工资。”
我“噗”的一声,差点没把嘴里的可乐喷出来。
两天的工资?就为我手上这瓶300毫升的“快乐水”?
我拿着那半瓶可乐,手突然有点抖。这哪是可乐,这分明是当地人遥不可及的“液体黄金”。在国内,这玩意儿就是三块钱的饮料,夏天打完球来一瓶,眼都不眨一下。可在这里,它成了一个衡量生活水平的残酷刻度。
那一刻,我之前所有关于“旅行的意义”、“体验异国风情”的文艺想法,全都被这瓶可乐给干沉默了。我意识到,我来到的,是一个用我们习以为常的逻辑,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。
而这,仅仅是个开始。
一、电,才是叙利亚的终极奢侈品
在国内,我们什么时候会意识到“电”的存在?大概只有手机电量低于10%的时候吧。我们对“24小时供电”这件事,已经习以为常到如同呼吸空气。
但在叙利亚,“找电”是我每天的头等大事。

大马士革的酒店,前台会给你一张“供电时间表”,堪比大学里的课程表,精准到分钟。通常是“来一小时,停五小时”的循环模式。
每天,我就像个参加“双十一”抢购的疯子。供电那一小时的信号声一响,我立刻从床上弹起来,把充电宝、手机、相机电池、电脑……所有能插电的玩意儿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全部插满。
然后,我就坐在那儿,眼巴巴地盯着充电指示灯,心里默念:“快点,快点,再快一点!”
那一个小时,弥足珍贵。我不敢洗热水澡,因为电热水器刚热就可能停电;不敢用电吹风,怕吹到一半断电,顶着个湿漉漉的头。那感觉,比我当年高考冲刺还紧张。
走在街上,你会听到一种持续不断的“嗡嗡”声。一开始我以为是空调外机,后来才发现,那是家家户戶必备的“神器”——小型发电机。
富人区,大功率发电机声音雄浑,像一头沉睡的野兽,保证家里灯火通明。普通人家,小发电机的声音就跟拖拉机似的,断断续续,带着点有心无力的喘息。
我和当地的朋友艾哈迈德聊天,他是个大学老师,月薪换算过来不到100美金。我问他,没有电怎么办?
他苦笑一下,指了指窗外:“听天由命。”
他说,晚上停电是常态。孩子们写作业,就点一支蜡烛。夏天最难熬,40多度的高温,没有空调,没有风扇,一家人就躺在地板上,彻夜难眠。
“那你怎么给手机充电?”我问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,瞬间觉得自己特肤浅。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太阳能充电板,巴掌大小。“白天放窗台上晒一天,晚上勉强能充个20%。看不了视频,但接个电话,回个WhatsApp信息,够了。”
我看着他手里的充电板,再看看我背包里那个20000毫安、能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的“充电巨兽”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在国内,我们抱怨的是5G信号为什么不是满格。在这里,他们祈祷的,只是手机能有电,能和远方的亲人报一句平安。
我们所谓的“电量焦虑”,在他们真正的“生存焦虑”面前,显得那么矫情,又那么奢侈。
二、手握一麻袋钱,买不了一瓶油的魔幻现实
在中国,我们已经快忘了现金长什么样了。一部手机走天下,扫码支付方便到连路边卖烤红薯的大爷都用得贼溜。
而在叙利亚,我体验了一把“亿万富翁”的快感,还是心酸版的。
因为常年制裁和战争,叙利亚镑的汇率,跟自由落体似的。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能差出十几倍。所以,所有外国人都会选择去黑市换钱。
我的向导带我钻进一条小巷,进了一个看起来像杂货铺的地方。我递过去100美金,老板从柜台下拖出一个巨大的麻袋,没错,就是装土豆那种麻袋,里面全是花花绿绿的叙利亚镑。
他抓出厚厚的一大沓,用验钞机哗啦啦地过了一遍,然后“啪”地一声拍在我面前。
那一瞬间,我感觉自己像电影里的毒枭在交易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堆在自己面前。我把钱塞进背包,包立刻被坠得沉甸甸的,感觉自己背了一块砖头。

可这种“富豪”的错觉,在我走进超市的那一刻,就碎了一地。
超市的货架,看着琳琅满目,但很多都是空的。一些基础物资,比如食用油、糖、大米,都用巨大的牌子写着“限购”。
我试着换算了一下物价。一公斤鸡肉,大概要花掉一个普通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。一升食用油,更是天价。
我看到一个当地主妇,在食用油货架前站了很久,拿起一瓶,看了看价格,又无奈地放了回去。最后,她只买了一小袋面粉和几个鸡蛋,手里攥着几张零钱,小心翼翼地数着。
那一幕,对我冲击巨大。
这要是在国内,我妈去超市,看到打折的油,那都是几桶几桶往家搬的,生怕占不到便宜。我们考虑的是哪个牌子的油更健康,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。
而在这里,他们考虑的,仅仅是“买不买得起”。
更魔幻的是,因为货币贬值得太快,很多商品的价格一天一个样。早上买的馕,可能下午就涨价了。所以人们一拿到工资,第一件事就是冲出去,把钱换成任何能保值的东西。
我那个背着一书包钱的“亿万富翁”,在超市里逛了一圈,最后只敢买几瓶水和一点面包。因为我知道,我每多花一分钱,可能都是在挤占一个当地家庭本就稀缺的生存资源。
那种感觉,真的太拧巴了。你明明手握巨款,却感觉自己一贫如洗。

三、一块烤馕的重量,我差点没接住
叙利亚人的热情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无论生活多艰难,他们待客的诚意,能让你瞬间破防。
我在阿勒颇古城里迷了路,一个正在修缮店铺的大叔,叫穆斯塔法,看我一脸迷茫,主动上来用蹩脚的英语问我要去哪。
聊了几句,他非要邀请我去他家喝杯茶。
这在中国,一个陌生人突然邀请你去家里,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:“这人是不是骗子?”但在那,我能感受到他眼神里的真诚,就跟着他去了。
他家就在古城深处,一栋石头老房子,看得出有些墙体是后来修补的,还裸露着水泥。家里陈设极其简单,几张垫子,一张小桌,就是全部的家具。
穆斯塔法的妻子端上红茶,还有一盘切好的西红柿和黄瓜,以及几张热气腾腾的烤馕。
他不停地把馕撕成小块,蘸上一点橄榄油和香料,递到我面前,用不多的英语单词重复着:“吃,吃,朋友,中国的,朋友。”
我知道,这可能已经是他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。
我象征性地吃了一点,连说吃饱了。在中国人的饭桌文化里,这是一种客气。主人会继续劝你,你再推辞几下,一来一回,是人情世故。
但穆斯塔法看我停下,眼神里流露出一丝焦虑和失望。他以为是他的食物不合我胃口。他急得开始比划,指指馕,又指指自己的心口,意思是这是用心做的。

我瞬间就明白了。我的“客气”,在这里,是对他真诚的一种误解,甚至是否定。
我赶紧拿起一块馕,大口大口地吃起来,还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他这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,又给我续上了滚烫的红茶。
临走时,他妻子还非要打包几张馕让我带上。我怎么都推不掉,只能收下。那几张馕,温热的,沉甸甸的,我拿在手里,感觉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重。
我差点没接住的,不是那块馕,而是那份在贫瘠生活中,依然选择倾其所有来待客的尊严与善良。
这让我反思,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富足了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有时候反而隔了一层精密的计算和客套的纱。一顿饭局,可能更多的是社交,是资源置换。
而在穆斯塔法家里,那顿简单的下午茶,没有功利,没有人情,只有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坦诚相待。
四、这里的红绿灯,只是个建议
聊完沉重的,说点有意思的。叙利亚的交通,那叫一个“狂野”。
在大马士革打车,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“速度与激情”。司机们个个都像是退役的F1赛车手,在拥挤的街道上见缝插针,喇叭按得震天响。
红绿灯?那东西在这里,基本就是个装饰品,最多算一个“建议”。绿灯当然要走,黄灯意味着“快点冲”,红灯嘛……只要没警察,左右看看没车,也照冲不误。

我坐在副驾,全程紧握着安全带,感觉自己的小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。好几次,我们的车头和旁边的车就差几厘米,我都准备好听那“刺啦”一声了,结果司机一个神龙摆尾,就过去了。
我问司机:“大哥,你们开车都这么猛的吗?”
司机一边叼着烟,一边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,乐了:“不快点,怎么赚钱?时间就是钱啊,朋友!”
这话听着耳熟,不就是我们国内“效率至上”的翻版吗?但在一个连电力供应都无法保证的地方,这种对“效率”的追求,显得既荒诞又心酸。
路上的车,也像个移动的汽车博物馆。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奔驰,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苏联时期老爷车,个个都“带病上岗”。车窗摇不下来是常事,空调基本是摆设,后备箱用绳子捆着也屡见不鲜。
但就是这些破旧的“铁疙瘩”,承载着一个个家庭的生计。
还有无处不在的军事检查站。每隔一段路,就会有持枪的士兵检查证件。一开始我紧张得要死,后来发现,他们对中国人异常友好。
只要看到我的中国护照,士兵们大多会露出笑容,挥挥手,说一句发音不准的“你好”,然后直接放行。
向导告诉我,因为中国在国际上一直主张和平,援助了他们很多,所以叙利亚人对中国人有天然的好感。
这种“刷脸”就能通过的待遇,让我这个普通中国公民,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“国家”这个词带给我的庇护和荣光。
在那个混乱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交通系统里,我看到了当地人顽强的生存法则:在规则的缝隙里野蛮生长,用自己的方式,为生活杀出一条血路。

五、废墟上开出的玫瑰,和一句“你好”
来之前,我对叙利亚的想象,就是满眼的断壁残垣,和人们脸上挥之不去的阴霾。
废墟是真的,随处可见。那些被炸弹撕开的建筑,像一头头沉默的巨兽,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。
但人的精神状态,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
在阿勒颇的古堡下,我看到几个孩子,在一片瓦砾堆里踢足球。他们没有球门,就用两块石头代替。足球也破了皮,但他们追逐着,叫喊着,笑声清脆得能穿透整个天空。
阳光洒在他们满是灰尘的脸上,那笑容,干净得让人心疼。
一个卖玫瑰花的小男孩,看到我这个外国面孔,跑过来,把手里最好看的一支玫瑰递给我,用生硬的中文说:“你好。”
我问他多少钱。他摇摇头,指了指我胸口的五星红旗小徽章,又指了指自己,笑了。
我愣住了。那一刻,我感觉手里的不是一支花,而是一整个民族的坚韧与善意。
在他们的世界里,昨天可能是生离死别,明天可能依然前途未卜。但他们选择活在当下,用尽全力去寻找哪怕一丝丝的快乐。

一个咖啡馆老板,店里的墙壁上还有弹孔,但他用心地在弹孔周围画上了花朵。他跟我说:“生活已经够苦了,我得给它加点糖。”
这种乐观,不是我们那种“没什么大不了”的鸡汤式口号,而是在见证了深渊之后,依然选择仰望星空的勇气。
他们会跟我开玩笑,会热情地分享他们的水烟,会好奇地问我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。他们谈论C罗和梅西,谈论最新的土耳其电视剧,就好像战争从未发生过一样。
但你知道,那种创伤是刻进骨子里的。只是他们选择不把它时时刻刻挂在脸上。
这和我们中国人很像,我们信奉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,习惯把苦难自己消化,展现给外人的,永远是积极向上的一面。
但他们的“消化”,是在一个更大的、更不可抗的命运背景下进行的。我们的苦,是发展的烦恼,是内卷的疲惫。而他们的苦,是生存本身。
六、‘理想’这个词,在这里有点太重了
在大马士革大学门口,我认识了一个叫萨拉的女孩。她英语说得特别流利,带着一点英伦腔,是在网上看英剧自学的。
她学的是英国文学,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。
我们坐在大学旁边的咖啡馆里,聊雪莱,聊莎士比亚。她的眼睛里,闪烁着对知识和未来的渴望。那样的神情,和国内任何一个优秀的大学生,别无二致。
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。

她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。“我不知道。也许,找个教英语的工作?但工资很低,可能一个月只有50美金。”
她顿了顿,说:“我很多同学,毕业就等于失业。有能力的,都想办法出国了。但出去,太难了。”
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
在中国,我们这代年轻人,最常抱怨的是“内卷”。我们为了一个好offer挤破头,为了KPI熬夜加班,为了买房背上三十年贷款。我们觉得很累,很苦。
但我们至少有一个清晰的上升通道。只要你努力,大概率能看到回报。我们烦恼的,是“如何过得更好”。
而对于萨拉这样的叙利亚年轻人,他们面临的,是“如何生存下去”的问题。
他们的才华、学识、梦想,被困在这个国家,被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。
“理想”这个词,对我们来说,是奋斗的目标。而对他们来说,可能是一种不敢轻易触碰的奢侈品。因为在理想之前,他们得先填饱肚子,得先保证家里的电够给手机充上电。
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无奈。个人的努力,在巨大的时代困境面前,显得如此渺小。
那天下午,阳光很好,但我和萨拉的对话,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。我看到了一个本该展翅高飞的灵魂,被无形的枷锁牢牢地捆住了翅膀。

结尾
离开叙利亚的那天,在去机场的路上,车窗外,一栋被炸毁一半的居民楼掠过。
就在那栋楼三楼的阳台上,没有窗户,没有墙壁,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水泥平台。
但就在那个平台上,摆着一盆鲜红的天竺葵,开得正艳。
旁边,还晾着几件刚洗过的衣服,在风中轻轻飘荡。
那一抹红色,和那几件飘荡的衣服,像一个顽强的感叹号,打在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。它在告诉我,即使家园破碎,即使生活艰难,但只要人还在,生活就得继续。
那盆花,和晾晒的衣服,就是叙利亚人最朴素,也最强大的宣言。
回到国内,降落在灯火辉煌的浦东机场,我打开手机,瞬间被各种信息淹没。同事在群里讨论着下个季度的KPI,朋友圈里有人在晒新买的车,有人在抱怨今晚又要加班。
一切都那么熟悉,那么正常。
我突然想起艾哈迈德在停电的夜晚点亮的蜡烛,想起穆斯塔法递给我的那块沉甸甸的烤馕,想起废墟里孩子们清脆的笑声,想起萨拉谈及未来时黯淡的眼神,也想起了那盆开在废墟上的天竺葵。
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们的生活,更没有权利去同情他们。因为在那样极致的困境里,他们所展现出的坚韧、乐观和尊严,足以让任何一个生活在和平国度的人感到羞愧。

我们总抱怨生活不易,但或许,我们只是忘了,我们所拥有的这个“正常的、安稳的、有电有网的”生活,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幸运。
而对于叙利亚的普通人来说,每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今天,都是他们需要拼尽全力才能换来的,一个值得庆祝的明天。
说几句公道话,真的,他们太难了。但他们,也真的,太了不起了。

